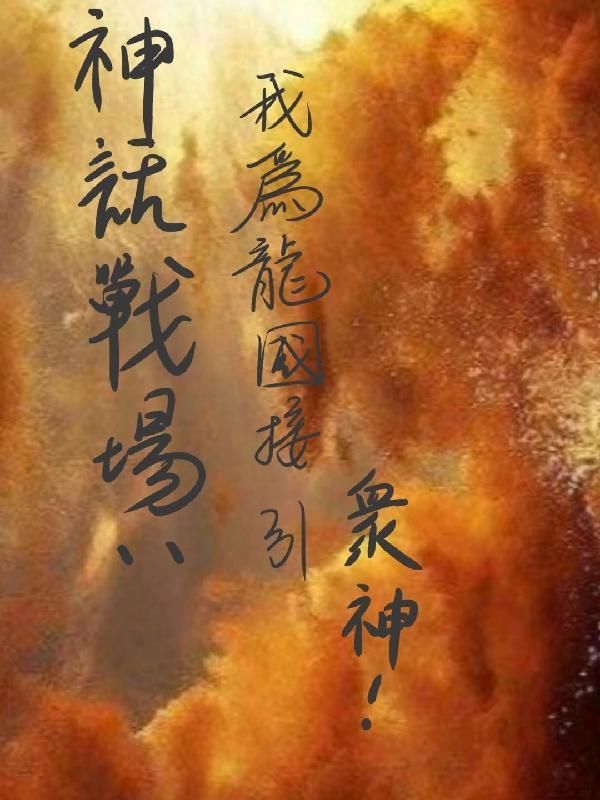深度文学网>谁说女主有人爱 > 第一百五章 箭矢(第1页)
第一百五章 箭矢(第1页)
他人见自己的小什长不但没有行打骂,反倒对自己关心备至,不由心怀感激。清云也趁机说了不少好话,又与几个兄弟称兄道弟,聊到酣处,顺便对月结拜,以弟兄相称。萱萱也从旁帮衬,两人一唱一和,只把余下的几人说的晕头转向,家里的事有的没的都抖了出来。清云也悄悄记在心中,已备将来所需。
可清闲的日子没过几天,便是繁琐的训练,清云会骑射,特别是射箭的本事在嵇乘云的帮助下已初具水平,但他毕竟从未参加过真正攻城拔地的野战,更没有混在军旅里,行进也不过当过哨兵,如今面对残酷的战士,还是心有戚戚。
她亲眼见着一批又一批伤痕累累的士兵被送回,他们年纪很轻,很多还是孩子,却被生生送上战场寻死,一场战事下来,血流成河,尸骨遍地,很多人难得捡来一条命,却缺胳膊断腿,从此再也没了站起来行走的机会,望着这些人身上的伤,清云就想起来多年前北山大营中遇到的兄弟,那时前一刻还活生生站在身边的人,后一秒就倒在地上,化为血水或肉块。他们瘫在地上连捡都捡不起来,更别提有机会安葬,大部分士兵都生长在乡村,从小受着身体肤受之于父母,人故后而安葬的传统教会,可努力了一生,到头来却连个坟都找不上,只能被抛尸在荒野之中,还真是让人觉得可悲可叹。
练了几日便到了上战场的日子,清云初来乍到,对战事并不熟悉,便打算混在士兵堆里,只求个安稳,可真正到了战场上,她才明白在乱局中独善其身有多么艰难。
战事一起,双方便引着精壮的铁甲兵前来,南方不似北地有骑兵,但人家有铁制的战车和面具,兵器雄纠纠气昂昂,便冲了过来,将先前的送命队冲的七零八碎。这些送命人都是奴隶出身,主要为战俘,还有少数民兵只有简易的装备冲在最前方给铁骑军开路,他们身着破衣烂衫,也没带什么刀具,只是靠着肉体对付那金兵铁骑,一群人浩浩荡荡过去,只余下一滩血水,就这样成了阵前亡魂,被敌方部队碾过。
接下来便是骑兵营踏过战友的尸骨冲锋,若骑兵守得住前方大营,便可以护卫城墙,否则再后退便到了真正残酷的攻城。万千骑兵在主将喝令之下,扬鞭向着敌方冲锋,万万剑矢破空而来,几乎看不清方向,不停有人中箭倒下,也有人向刺猬一样背上身前全是箭,却依旧拼尽全力坚持,任凭专心的切肤之痛传来。在这些濒死的人中间,清云护着自己的前胸与头部四处找空钻,萱萱在不远处鼠窜,两个人就连拉弓射箭的勇气都没有,好在战马还算通人性,也没闯下幺蛾子,勉强载着两人在漫天飞剑中驰骋。
一场战事下来,清云甚至不知道生了什么,她茫然的像个木偶一样混在人群里,不知道有多少同伴的血溅在了自己身上,她的手在抖,肩膀被弓箭磨得身疼,两手也被缰绳勒出血,眼前全是红色,海一般波澜壮阔的红色。
她几乎辨不出其她的颜色,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左摇右摆以躲避进攻,也如何在不小心之下踏死了己方摔下马的士兵,她只是跟着人群向前冲,因为她没有回头的机会,不必再在千军万马中如何绕过人群回头,就算能驶回原处,也会因违背军令被一箭射死,战场上容不下逃兵,她只能迫于无奈在死人堆里穿梭,整个人脑子像是蒙了一层雾。她一切行为都处于自保本能,当撤退的号子响起时,她也踉踉跄跄的随着向后退却回到营帐,身边全是哭嚎与叫喊,之前所见的兄弟此刻在地上挣扎,血染红了大地,他们像虫子一样扭动,断掉的四肢甚至在地上弹起,溅起了一阵血雨,那些可怜的孩子不停的哭嚎,在地上翻滚,军医尽力去救,却毫无作用,一个又一个生命就这样消散在血红色的傍晚。
月亮升起,空中拂过一阵清风。乌云骤起,凉凉的雨丝打在身上,打在冒着血的伤口上,打在麻木的脸颊上,像血,像眼泪。黏黏糊糊的带着浓郁的血腥气,也冲刷着地面上的罪恶与死亡。
清云的双腿已近乎迈不动,她的双手还能动,几乎是跪在地上木然地爬向那些倒地的士兵,将他们拖到营地,交由军医。他们的血染红了她的,她的衣裳,她也染红了她的双眼,她在地上爬行,身体呈现扭曲的姿态,在血海里宛如一条搁浅的鱼,因为拖着铠甲,她的食指已经开裂,血从中渗出,很疼,但她已经成了口不能言的傀儡,失去了一切知觉。那些死人就被拖到路旁,堆成一座山,他们的外衣被扒下,能用的继续给予活人,他们的刀剑也一一摘下,扔给尚且有呼吸的士兵,那些还如行尸走肉一样喘息的人们就那么冷漠的注视着曾经活生生的弟兄,扒开他们的衣裳,沉默的搜索他们因缺乏营养而干瘪的身体,最终将他们运走,有的做肥料滋润田亩,有的烧成灰,以防占用活人的地盘。
没有人在意死者的名姓和家人,没有人在意他们曾有的喜怒哀乐,他们赤裸裸来到这糟糕的世界,也就一无所有的离开,还不如死在污水里的死狗。世界便是残酷如斯,没有半分温情,步步退让的战事终于到了尾声,但清云已经失去了活气,她颤颤巍巍犹如迟暮的老人爬到营帐旁边的沙地上,坐下怔怔的望着,对着远方某处不知名的光点呆。日暮的晚霞在身上画出一幅清新明亮的画图,雨过天晴的彩虹也在空中架起一座天桥,五光十色,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她抬起昏昏沉沉的头颅,努力的想看清楚天上的场景,却终是没办法睁开,难以保持视线清晰的眼睛。
正在沉默的当口,她忽然听到一阵轻微的唾泣,转过身,她看见萱萱正坐在不远出的沙地上,低头啜泣。清云有些回过神,想拍拍她的肩膀,问她怎么样,可嘴却无论如何也张不开。
就在这时,阿潇的声音传来,她也半是爬行的过来,身上有明显的伤口,一双好看的眼睛此时也失了光泽,其中只余下深深的恐惧,她和慕雨互相搀扶,总算是一路过来见了清云。她抬手擦了擦眼睛,嘴抖了好半天,也没说出只言片语,最终还是慕雨小声说:“哥,咱还在这里带着吗?我是冲在前面那小兵,这战士太惨烈了,咱还是回山上去,虽然招不上兵马,但至少能活着,不然我担心。”说到这里,她低着头没再往下说,这姑娘是铁匠出身,以前一直做冶刀的事,力大如牛,也上过战场,但当时大楚尚有余力,不像如今背水一战时战况之惨烈。
清云知道她的想法,正想点头放她走,让她假装尸体潜出去,却听得身旁吓得哆哆嗦嗦直哭的萱萱此刻止了泪,爬到同伴身边,轻轻张开双臂抱住她,声音是前所未有的温柔:“咱俩人受过苦,本是不怕死的,到了这步做逃兵败将实在没意思,大哥心疼放你走,可上了苍山就有活路吗?跟着朝廷是死,跟着农民起义军是做妓子,终逃不过一死,也就只有自立门户,可咱自立,人家可不认,没有辎重兵力,终是逃不过。大哥在想办法混进来找些兵丁一起起事,靠抓他们老娘姑娘,让他们忠心,这是唯一的路,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如何呢?”
慕雨闻言头始终没抬,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她嘴唇翕动,过了很久,小声道:“我明白,如今天下大乱,正是人皆欲为王,若尧舜之道不行,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永无出路,我家里还有老娘妹妹,我想拼一把,哥说的对。”
阿潇也点了点头:“对。我们一直在民间流浪也深知如今的天下是多黑暗。谁都想活,可在哪不是毫无希望?跟着哥没错的。”说罢,她拍了拍清云的肩膀,露出了一抹算得上灿烂的笑容。清云勉强扯开嗓子,喉咙里依然弥漫着浓烈的心气,她努力让声音显得清晰:“放心,没问题的,我们坚持下去会找合作的契机,回了山上也是等死,没有武力,连个狮子也打不过,更别提人家各国的军队,别提那些兵马车炮的进攻。”
实话实说,她有些后悔了,后悔为何要起事,为何接受这些生死存亡之事。她本可以安安定定的和雀儿、阿芝和阿潇生活不必关心这些天下大事,天下人的存亡本不是她的责任,她为何以命相搏?
可是望着那些冲在前面的肉墙,望着尸骨遍野的战场,望着姐妹们充满希望的神情,她就动摇了。她多希望自己可以生长在一个至少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和尊严的世界,过一种像人一样站着活的日子,可很明显没有人可可以带给她这样的生活,她只有用刀剑用着单薄的血肉之躯杀出一条血路,无所畏惧的向前,因为她还有希望,因为她还有雀儿,她想让那个姑娘好好的长大,而不是像自己一样流浪一生。她希望这孩子至少比自己过得好,可那些人只会奴役她,只会用铁骑碾压她脆弱的身躯。只有自己可以站在她的立场上,为她想,让她永永远远幸福下去,像个自由的精灵。和雀儿一样的孩子很多,每个孩子都应该自由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