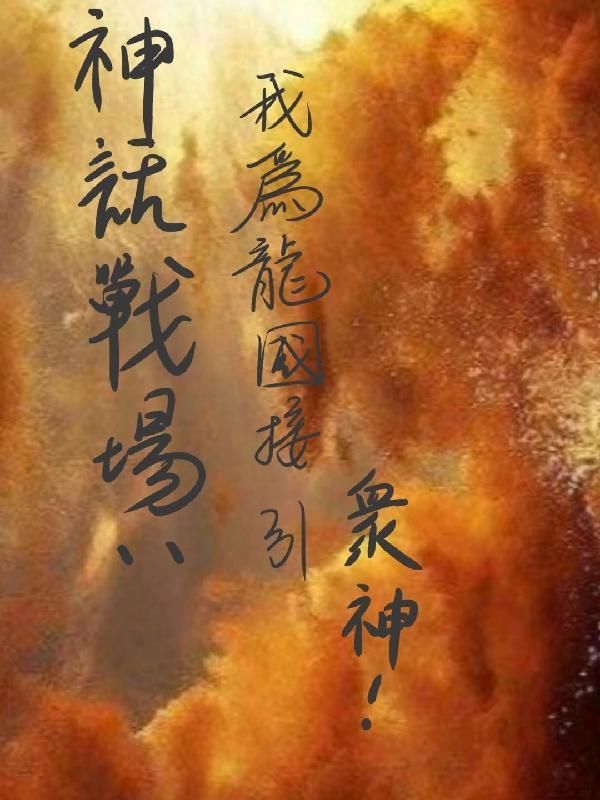深度文学网>明尊 > 第一百八十一章 九龙宝船入龙渊(第1页)
第一百八十一章 九龙宝船入龙渊(第1页)
六十八岁的王老爷子站在钞关浮桥之上,四下里空无一人,只有他们一行人在浮桥之上打起火盆。
自从那日里,红楼鬼船冲撞了此地,桥墩上挂满了钞丁,晚上就再也无人敢走这座浮桥了。
王老爷子穿着新的白褂子,新理的头,鬓角剃的干干净净,拿着金纸往火盆里送。
“这扎纸王的手艺不寻常,他家的金纸是柞树皮,配上数十种香药,经过九千九百锤秘法制成的,最是灵验,半个直沽城烧纸都从他那买,但这真货啊!他只卖给行家。咱们走阴人礼多鬼不怪,宁可繁琐一些,家伙事也要齐全,说不准,就能保你一命……”
“往年这样的大活,怎么也要把三牲六礼给备齐全了!”
王老爷子絮絮叨叨的跟身旁的小伙说着,那小伙面露难色:“爹!”
他响亮的叫着,随即小声道:“那扎纸王是白莲教的逆贼,铺子都叫官府给封了!你说话也小声些,别让衙门的人听去了!”
王老爷子手一颤,苦笑道:“也是,你继承了我的香火,也算是给咱老王家留了一条后,这走阴的邪门营生,就别干了吧!”
王老爷子将一双黑布鞋小心脱下,新的白袜子踩在地上,他将两只鞋扔起。
只见两只鞋一前一后,翻了个面,一只搭在另一只上面。
王老爷子微微一愣,捡起来再扔了一次,下一次,一模一样的情形再次出现在老爷子的面前。
如此三次,都是一模一样的结果,老爷子双手微微颤抖。
旁边戴眼镜的四眼道长叹息一声,侧头低声问张三指道:“我们南方有扔卦的,一阴一阳是圣杯,代表神灵同意了!这样子,是不是神灵不同意他走阴?”
张三指面色复杂:“走阴有个规矩,过阴时,榻下双履,必一仰一覆,尽仰其履则死不复返!”
四眼道长看着双手颤抖着一次次扔鞋的王老爷子,面露不忍之色:“神灵不同意,这是大凶之兆!何必勉强?”
张三指没有说话,只冷冷看着王老爷子满头大汗,一次次的布鞋掉下来,每次必定双双覆起,一连一十八次,无一例外,王老爷子失魂落魄,苍白的头湿漉漉的,冷冽的江风亦难以吹干。
他颤颤巍巍的跪下,磕头道:“祖宗在上!”
“不肖后辈王穷剩,穷鳏无后,乃断送祖宗血脉的大罪!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如今托人寻回一点血脉,重续人伦,受人所托,最后走一回阴路,不敢求祖宗庇佑……只请祖宗看见,王家又有香火了!穷剩死不足惜,但愿祖宗保佑王家香火绵延,若有后辈贤愚不肖,未能传承血脉,亦或谋害王家后人者,吾身堕九幽亦化为厉鬼纠缠!”
王老爷子越说,声音越急厉,旁边的儿孙闻言浑身一颤。
他决绝的抛起第十九次鞋子,这一次,终于一正一反,王穷剩一个响头磕下去,鲜血染红了那一块石砖。
张三指冷冷的看着这一幕,眼中并没有什么动容,直到王老爷子拿起了惊魂锣,披上了人皮衣,提着一面白灯笼,他身后的孝子领着一位六七岁的男孩,捧着个小包裹。
男孩看着这一幕,怯生生的喊了一声:“爷爷!”
王老爷子的脸色这才柔和了一些,摸摸孙子的脑袋,他吩咐道:“把大爷请出来!”
男孩这才从怀里的小包裹里,拿出一尊瓷娃娃,憨态可掬的样子,白底的瓷胎,描了黑色的眉眼,在旁边的白灯笼苍白的烛光下,显得越清冷。
泥娃娃生动可爱的眉眼,这一刻显得如此的古怪而缺乏生气。
系着娃娃的红线,也成了黑色的墨线,一头拴着娃娃,另一头系被男孩小心在了王老爷子的手腕上。
“打灯笼!”
张三指冷冷吩咐了一声,运河两岸,顿时亮起一盏盏白灯笼。
一排排白灯笼倒影在水面上,只见河水泛起波澜,就如同一艘艘沉重的货船破开水面,掀起的浪花,一条条水痕从远处划来,犹如九根利箭破开平静的南运河水面。
漕帮的弟子举起白色的麻布棋幡,如同往常一样引水,指引那无形的阴船停靠在码头。
“卸货!”
漕帮弟子一声大吼,一个个赤裸身躯的脚行青皮,挑着一个个沉重的担子,但江风吹开黑布覆盖的一角,分明只是一件件纸扎的金银珠宝,车船马楼。
王老爷子只看了一眼,便微微惊讶的抬头。
张三指点了点头:“老爷子,这都是送你路上打点的,他白莲教的确是强龙一条,但我们这地头蛇也不是白混的,区区一个扎纸王,我端了他的铺子,三十年积累的冥宝,都在这了!”
脚行的弟子挑着扁担,来到了码头,一个接一个的往河中跳去,连水花都没掀起来,就沉入黑漆漆的河面里。
河面之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两个担子被放了下来,上面纸扎的鸡鸭鱼肉,拨浪鼓,虎头帽,洋画片,小衣服,堆了满满两个箩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