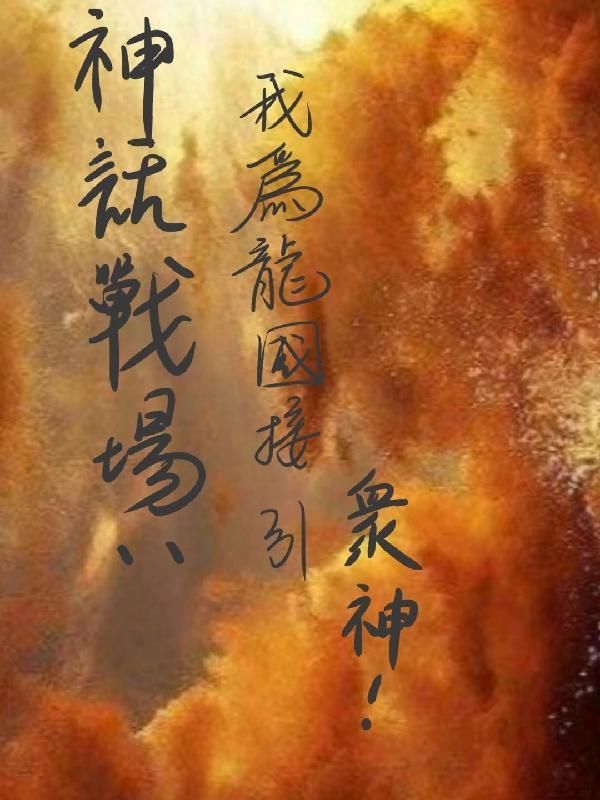深度文学网>第三十年明月夜 > 第34节(第1页)
第34节(第1页)
李楹愕然的瞪大眼睛:“他是畜生吗?他和崔珣的恩怨,他找崔珣去呀,为什么要牵扯另一个无辜女子?”
鱼扶危也觉得很愤然:“是!不管沈阙多么厌恶崔珣,他都不应该为了报复崔珣,去欺凌一个沦落风尘的可怜女子!这般做法,简直非人所为!”
李楹想起了盛阿蛮的阿兄,鬼将军盛云廷,他魂魄脱离桎梏的第一件事,就是纵马扬鞭,直奔大明宫,只为了求圣人发兵襄助被围困的天威军,挽救危在旦夕的关内道六州,他到死都想着让大周国土不失一寸,可这般忠肝义胆的盛云廷,他唯一的妹妹,居然被他守卫的国家权贵这般欺凌,李楹咬牙,眼眶不由阵阵发红:“沈阙,他真的该死!”
鱼扶危也义愤填膺:“谁说不是呢?一个男人,找女人撒气,某真是看不起他!”
“那崔珣呢?崔珣知道吗?”
鱼扶危点了点头:“崔珣他自然知道,某打探到,崔珣知晓之后,目眦欲裂,当即提鞭直奔国公府,将沈阙鞭打的满身满脸是伤,听说沈阙也不求饶,他只是冷笑,说道:‘崔珣,你听着,盛阿蛮是因你而遭难,你这辈子,都别想过这个坎!’”
李楹愤懑到眼前一片眩晕,差点栽倒在地,鱼扶危赶忙去扶她,她却一把抓住鱼扶危衣袖:“然后呢?他杀了沈阙吗?”
鱼扶危不忿的摇了摇头:“没有,沈阙家仆去大明宫求救,金吾卫知悉后,将崔珣和沈阙都带入大明宫了,如今还未出来。”
“我要去……”李楹抓着鱼扶危的衣袖,稳住摇摇欲坠的身躯,她喘着气,对鱼扶危说道:“我要去丹凤门,我要去等一个结果。”
这一等,便从晨光熹微,等到了日暮风寒。
小雨淅淅沥沥而落,滴打在大明宫青绿色琉璃重檐之上,李楹站在丹凤门外,她目不转睛,定定看着紧闭的朱红宫门。
她在等宫门打开后,到底是谁出来。
她身旁,鱼扶危忍了又忍,最终还是忍不住道:“虽然沈阙干了这猪狗不如的事情,但是他不会有事的,数年前,他因与淮安王有怨,就故意诱奸了淮安王未过门的妻子,让淮安王蒙受奇耻大辱,淮安王上告圣人,沈阙也只是象征性的被罚了点俸禄,王族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贱籍乐姬呢。”
李楹眼神茫然,细弱雨丝顺着斜风飘落,打湿了她长如鸦羽的睫毛,鸦睫挂满微密雨珠,她眼前如蒙上一层轻纱,雾蒙蒙的看不清前方光景,她懵懵的摇了摇头:“不,阿娘和阿弟会杀了沈阙的。”
鱼扶危深吸一口气,他苦笑道:“他们是你的阿娘和阿弟,但他们也是大周的太后与圣人,历朝历代,没有一个太后,也没有一个皇帝,会为了一个妓女,去杀了皇亲国戚的。”
李楹张了张口,她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反驳,她其实知道,鱼扶危说的是对的,阿娘和阿弟,是不会为了盛阿蛮,杀了沈阙的。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从她心头涌现,除了无力,还有几分绝望,她在为盛云廷觉得绝望,更为盛阿蛮觉得绝望,还有,为崔珣觉得绝望。
朱红宫门终于缓缓开启,浑身上下都被鞭笞到血迹斑斑的沈阙被肩舆抬着,出了大明宫,他俊美面容上也有数道被鞭打出来的血痕,看起来甚为可怖,但疼痛若此,他嘴角却始终挂着讥诮笑意,仿佛有一种恶气得出的快意一般,他蔑视般的回头望了眼巍峨气势的大明宫,然后对抬着肩舆的家仆说道:“走吧,回去办喜事了。”
沈阙出大明宫良久后,崔珣才出来,他脸色是纸一般的苍白,身体也在微微颤抖,他看到了鱼扶危和李楹,但是他却没有像那日晚上一般恼火不快,而只是看了两人一眼,就木然向前而去。
李楹抿了抿唇,她追了上去,亦步亦趋跟在崔珣身后,鱼扶危苦笑了一下,他自嘲的摇了摇头,然后便往反方向而去。
斜风细雨,崔珣绯红官服已被雨水浸湿,紧贴在身上,显得他身形愈发瘦削,李楹默默跟在他身后,一阵寒风吹过,崔珣忽掩袖剧烈咳嗽起来,李楹脚步快了快,几乎要走到他身旁,但她又突然放慢了脚步,还是那般亦步亦趋,安安静静的跟在他的身后。
崔珣没有回崔府,而是去了东市一家酒坊,酒坊主人认识他,战战兢兢的给他领到了最好的厢房,又上了最好的酒,崔珣于是就抓着酒注,往口中灌着酒。
一壶接一壶的烈酒都被崔珣灌入口中,他喝的太急,酒液呛到喉咙中,又是一阵剧烈咳嗽,李楹本来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陪着他,但见到此景,也忍不住去拿过他的酒注:“不要再喝了。”
崔珣原先惨白的脸色因为酒液倒染上几分酡红,如夕照晚霞般绮丽秾艳,但李楹分明看出了那绮丽秾艳背后,藏着的无尽悲凉。
崔珣伸手,去向她索还琉璃酒注,李楹却摇了摇头,将酒注藏在背后,她道:“我知道,你想早点喝醉,醉了,就能忘记阿蛮的事了,可是,醉了,不是还会醒吗?难道醒来后,一切就会没有发生过吗?你为何不想想,若你今日醉死在这里了,那阿蛮还能依靠谁?”
崔珣听罢,却只是喃喃道:“她依靠不了我,我也护不住她,圣人已经下旨,让她嫁予沈阙为妾,我,无能为力。”
李楹一惊:“哪有这种事情?施暴者未受任何惩罚,反而要将受辱者送给他继续受辱?这是哪门子道理?”
“道理?”崔珣轻笑一声:“这世间,哪有道理二字,有的只是大局二字,一个乐姬,一个国公,一个孤女,一个将军,一个轻如鸿毛,一个重于泰山,道理?哈哈,道理?”
他说到最后,已是满腔愤懑,喉咙一阵腥甜,他捂嘴咳嗽,咳到后来,掌心已隐隐有一缕殷红血丝。
李楹唬的魂飞魄散,她扔了酒注,抓住崔珣的手掌:“崔珣,你……”
这个“你”字一开口,她就哽咽难言,豆大泪珠也顺着脸颊滑落,砸在崔珣掌心,崔珣怔了一怔,他忽从李楹手中抽出手掌,说了句:“死不了。”
李楹咬着嘴唇,她抹了把泪,说道:“沈阙的话,杀人诛心,他说是因为你,阿蛮才会遭遇这一切,可是,是他禽兽不如,是他欺凌弱女啊,他凭什么将他的错误,反推到你的身上呢?你不要因为他的话,这样折磨自己。”
崔珣听罢,却惨笑一声:“不,他说的对,若非因为我,阿蛮根本不会遇到这种事,是我没有保护好阿蛮,我愧对云廷,不,不止云廷,我愧对所有人。”他脑海中,又想起哑仆比划的那句话:“曹五郎的母亲,不堪受辱,上吊而死。”
他指节攥的发白:“六年了,已经六年了,若这六年,我能给他们昭雪,他们的家人,也不会被这般欺侮,我真是,无用至极!”
崔珣此刻内心,已经极度痛苦,刚刚灌下的几壶烈酒如今后劲上来,他头脑愈发昏沉,趴在紫檀酒桌上喃喃道:“我救不了他们,救不了他们的家人,我也救不了我自己。”
李楹眼中含着晶莹泪珠,她轻声说道:“崔珣,你不要这样,崔珣。”
崔珣伏在桌上,漆黑双眸看着李楹,她脸庞清丽,如天上明月,他忽又喃喃说了句:“你也救不了我。”
说完之后,他便闭上眼睛,沉沉醉了过去,只是眼角,却无声地滑落下一滴泪水。
李楹并没有听懂崔珣最后那句话,她内心也被极度的痛苦所充盈,她没有接触过天威军其他人,但她接触过盛云廷,接触过盛阿蛮,盛家兄妹,一个忠君爱国,一个敢爱敢恨,但是他们的结局,却一个比一个惨烈,而她,根本帮不了他们。
李楹心中,快要被满满的无力感压垮,几乎要无法呼吸,她只面对两个人的血与泪就这般痛苦,崔珣却是要面对整整五万天威军,以及他们家眷的血与泪,那他,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六年的日日夜夜,他该如何痛苦?
李楹胡乱擦拭掉自己脸上泪痕,她看着酒醉的崔珣,他醉着的时候,也是眉头微微皱起,仿佛梦中也有极度难受的梦魇折磨着他,他醉之前忽然说,李楹也救不了他,李楹虽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仍然伸出手,指尖轻轻拭去他眼角的泪水,她轻声说道:“不,我一定会救你的。”
第50章
两日后,国公府敲锣打鼓,十里红妆,去教坊迎娶了阿蛮。
这其实也是太后与圣人的意思,两个四品官员为了一个妓女大打出手,而且这两个四品官员,一个是天下高门之首的博陵崔氏,一个是当今圣人的表兄,简直是丢人现眼,不但丢崔珣与沈阙两个人的脸,更丢大周朝的脸,若传到番邦属国去,让圣人的颜面何存?
按照左仆射卢裕民和右仆射崔颂清的意思,是要杀了阿蛮,以正清风,以儆效尤,卢崔两派,分属朝中两大党派,两人都要杀了阿蛮,就等于群臣都赞同杀了阿蛮,圣人也有此等想法,不过敕旨将下之时,珠帘后的太后却悠悠说了句:“两个男人打架,倒要杀一个女人了事?”
众人面面相觑,因为太后这句话,阿蛮的性命是暂且保住了,但左仆射卢裕民最是固执严肃,他说道:“先秦有西施用美人计葬送吴国江山,汉朝有貂蝉施美人计挑起董吕矛盾,自古红颜最是祸水,盛阿蛮被崔珣和沈阙相争后,名声必定大噪,将来门庭若市,少不得还有其他官员效仿崔沈二人,长此以往,我大周朝堂还有宁日?”
杀不得,又放不得,群臣激烈争论后,一致认为既然沈阙占了阿蛮身子,那就让他将这个红颜祸水带回家去,好生管束,对于一个教坊乐姬来说,能脱离贱籍,做国公的侍婢,算是她上辈子烧了高香了。
至于崔沈二人,应该一人罚一个月俸禄,以示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