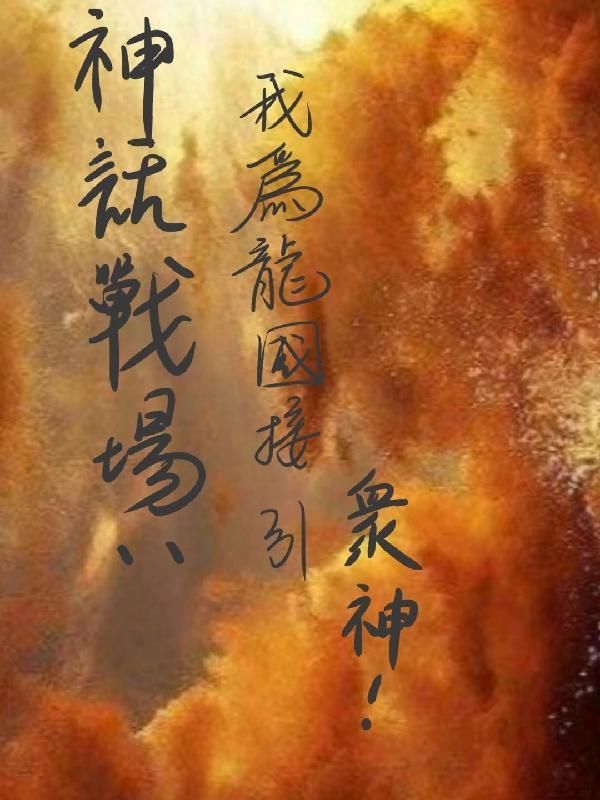深度文学网>森之迷宫 > 第9章(第1页)
第9章(第1页)
此刻罗劲松与楚向宁正并肩躺在黑暗里,这情景,让罗劲松想起了小学时候。
有好几次,玩得晚了,楚妈妈不放心他一个人回家,就会打电话给罗爸爸报备一声,然后留他在家里过夜。他就和楚向安、杜俊华一起在小屋的地板上打地铺,也是这样在黑暗里并肩躺着,彼此诉说着烦恼、秘密、理想,直到昏昏睡去。
那时他和楚向安是同桌,虽然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好动一个好静,却难得的很是要好。楚向安的家与学校只隔着一条马路,中午都是回家吃饭。有次楚妈妈来接儿子,看到罗劲松一个人,便很热情地将他带回了家。只一次,罗劲松就彻底爱上了那个楚姓家庭,并打定主意自此赖在那了。
其实楚家的饭并没多好吃,甚至可以算是简陋了。当年罗劲松一天有五块钱伙食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普通人的月工资也不过一两百块,五块钱足够大鱼大肉地挥霍了。他爱上的,只是那种热闹、随意而又亲切的氛围。
罗劲松的妈妈死得早,爸爸又一直忙于生意,父子俩连正正经经坐在一起吃顿饭的机会都少之又少,更别提关怀和谈心了。诸如他考试得了几分、在学校和同学是相处是否融洽、添了什么兴趣爱好之类的问题,罗爸爸都无暇顾及。罗爸爸全部的要求,就只老实念书,健康长大,将来子承父业做好生意罢了。
而罗劲松童年缺失的一切,竟都神奇地从楚向安家找了回来。楚爸爸楚妈妈是从事音乐教育事业的,本身就比普通的家庭更重视与孩子的交流,又比别的成年人多了一份活力和耐心。印象里,每天中午吃饭都是一大桌,除了他们一家人,罗劲松自己,还有寄宿在楚家学钢琴的杜俊华。后来楚妈妈表姐的儿子季临转学过来,也加入了这个行列。那时夏桥与季临算是青梅竹马,偶尔也一起来玩。
饭桌上总是有说有笑的,每人讲述稀奇的经历和见闻,大家再各自发表看法。连楚爸楚妈遇到事情,也会虚心听取孩子们的意见,一派民主而融洽的气氛。
罗劲松从小就很机灵,惯会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一来二去,不但认了楚妈妈做干妈,还极勤快地帮着做家务,采买东西。干妈做饭,他就在一旁打下手,干妈有事要出门,他就帮忙带着两三岁的楚向宁。后来楚向安和杜劲松双双考进了音乐学院附中,开始了住校生活。季临的父母结束支边工作回了城,季临也搬走了。只有罗劲松,一如既往长在了楚家,甚至楚向宁上小学的时候,他还以哥哥的身份去开过家长会。
想到这些,罗劲松一阵感喟。才眨眼功夫,小肉球楚向宁怎么就长成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了呢!那小时候咯咯咯蹒跚着跑过来要人抱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般。转念想想,又自嘲地笑了,自己转眼不也奔三了,时光真是催人老。
他侧过头,借着月色打量楚向宁,那小子很舒服地卷成一团,呼吸平稳,想必早已睡着。罗劲松悄声起身,把外套拉过来盖在楚向宁身上,若有所思地端详一阵,这张脸仔细瞧去,依稀还有几分小孩模样,光洁紧致、眉目分明,嘴角微弯一副笑摸样,上唇调皮地轻轻嘟起,透着年轻人特有的粉润光泽,仿佛某种牛奶味道的软糖,让人忍不住想凑上去品尝一番。
罗劲松一时忘情,小心垂下头颈,靠近那散发着甜美气息的诱惑唇角,呼吸渐渐纷乱……忽然,他的目光落在楚向宁枕在脸侧的左手臂上。在那里,有一条肉色疤痕,从手肘下方直延伸到手背。罗劲松的手轻轻触摸上去,疤痕如蜈蚣样微微凸起,使他的手仿佛被烫到一样,猛地一抖,赶紧缩了回来。一阵心烦意乱之下,罗劲紧翻出香烟和打火机,轻手轻脚钻出了帐篷。
随着罗劲松脚步声渐远,楚向宁浓密的睫毛抖了抖,缓缓睁开眼睛,目光望向昏暗的帐篷顶,幽幽地,叹了口气。
季临与杜俊华都还没睡,虽然喝了不少酒,尤觉不尽兴。这半年对所有人来说都过于压抑了,还好酒能让人暂时忘掉烦恼和不愉快,坦然地面对很多事。
杜俊华喝了一大口啤酒,闭着眼睛问:“向安还好吗?”
季临拧紧眉头:“好不好又如何……二十年呐,太漫长了。换做是我,一定撑不下去。”
沉默片刻,杜俊华有一搭无一搭地说:“大临你发现了没,小弟长得越来越像他哥哥了。”
季临轻抿了抿嘴:“很像,又完全不像。向安给人的感觉,仿佛密林深处的寂静湖泊,而向宁,却总让人联想到夏日清晨的阳光和海浪。”
“呵,还真是这样。”杜俊华赞同地点点头。
“花儿!”季临忽然有些郑重,“我一直想问你……你……还喜欢夏桥吧?”
杜俊华一愣,低头不语。
季临看了他一眼,坦率地说:“这么多年了,你怎么想大家都知道,你要是现在追她,我不会介意的。她一直以为我是怪她执意报警才不肯原谅她的,其实不是。”季临苦笑了一下,“那天晚上我约她出去本来就是要说分手的。只是临时喝醉了,没能赴约而已,然后就出了夏朵那件事。我其实……根本就不喜欢她,和她在一起,都是外公和舅舅的意思。我不想一直被别人支配命运,最后和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
杜俊华摇摇头叹了口气:“还好你没跟她坦白,否则她会更难受。她早就怀疑你是为了她爸的权利才和她在一起的。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敢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