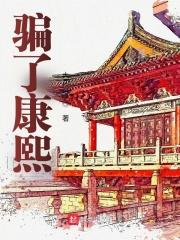深度文学网>我的铜镜通古今,装神明,包假的 > 第二章 向神明祈愿(第1页)
第二章 向神明祈愿(第1页)
邢家妇孺众多,被分配在了一间破草屋里。
沈玉瑶来不及解释什么,将所有的水囊都收集了起来,朝着邢恕那边赶去。
“小七,我也不知道你这铜镜是何来头,但这一路上人多眼杂,万分凶险,你可一定要注意着些。”
邢恕看着铜镜,眼神有些发直,显然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而且因为天气原因,燥热的空气早就将他身上的牛乳烘干。
以至于他现在就是一堆臭烘烘的流放犯里,唯一的香宝宝!
沈玉瑶将水囊全都接满,震惊过后又遗憾的看了邢恕一眼。
“可惜了,倒是让你先洗了一个牛乳浴。”
邢恕:“?”
是他想吗?
“三嫂还是先回去给娘,还有几位嫂嫂和侄儿侄女解解渴吧。”
他想静静。
沈玉瑶回到老太太身边,将水囊往她嘴边凑了凑,低声了几句。
老太太浑浊的双眼‘唰’的一下就流出泪来,凭着一股意志翻身跪下磕头。
“神灵保佑,终是不忍看我邢家忠肝义胆被辜负,得以降下神恩,我等诚惶诚恐,愿以我血肉和灵魂献上此祭,佑我族平安康健!”
“娘!您这是做什么?”
“祖母?”
老太太抹了抹脸,虚弱的摇了摇头,眼里却绽放着异色。
“你们的丈夫和父兄在天有灵,我们一定要活着走到最后。”
作为侯老夫人,丈夫和几个儿子战死沙场,还被诬陷通敌卖国,这冤屈属实咽不下去。
离京半月,日行五十里,要不是想着自己还有小儿子和这一大家子,她早都撑不下去了!
沈玉瑶将几个水囊发下去,迎上他们震惊不解的视线,摇了摇头。
“娘,好喝,香香的,甜甜的。”
“嘘!婉儿只能自己悄悄的喝,不然就会像白天那个哥哥一样。”
邢清婉才三岁,小小一只乖巧的窝在娘亲怀里,在侯府养出来的小奶膘也没了。
当初侯老夫人是想让她们几个儿媳自请下堂,总比带着孩子守寡来得好。
但几人就像是串通好了一般,一个都不愿意离开,生要做邢家的媳,死要做邢家的鬼。
若是换做以前,老妇人肯定笑着骂她们一顿,然后再好好奖赏一番。
如今,她只剩满心的感恩和酸楚。
可怜她的几个孙子孙女小小年纪,也要受这非人的苦难。
邢清婉迈着小短腿来到老太太身边,抱着自己的水囊要给她喂水。
“祖母不哭,婉儿不说,这是秘密,否则就会像那个哥哥一样见不到娘还有祖母了。”
老太太心疼的将她小小的身躯搂紧怀里,看向几个儿媳妇。
“现在不是时候,等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们”
事关邢家和大烨最大的秘密。
沈玉瑶有些担忧:“娘,小七那边?”
老太太神色莫名:“那是他的机缘。”
邢恕听了沈玉瑶的传话,点点头:“知道了,多谢三嫂。”
待人离开,他才细细的摩挲着手里的铜镜。
自打他记事以来,这块铜镜就一直同邢家的列祖列宗一起被供奉在祠堂。
小时候他不懂,差点弄丢了铜镜,被父亲狠狠打了一顿,罚跪三天。
只知道这铜镜对邢家来说意义非凡,铜镜在,邢家便在。
所以,这是受了邢家几代人香火供奉的祖宗显灵了?
不不不,如果真的是祖宗显灵。
那为几十万大军压境围剿父兄的时候,不显灵?
为何在他们被困数月,粮草断绝的时候,不显灵?
如果真的有神明,那为何不看看这昏庸的世道下,兵祸连连,扶棺领军,神鸦社鼓,岁乱相食!
邢恕手上的伤口因为他的用力导致裂开,鲜红的血液顺着掌心浸入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