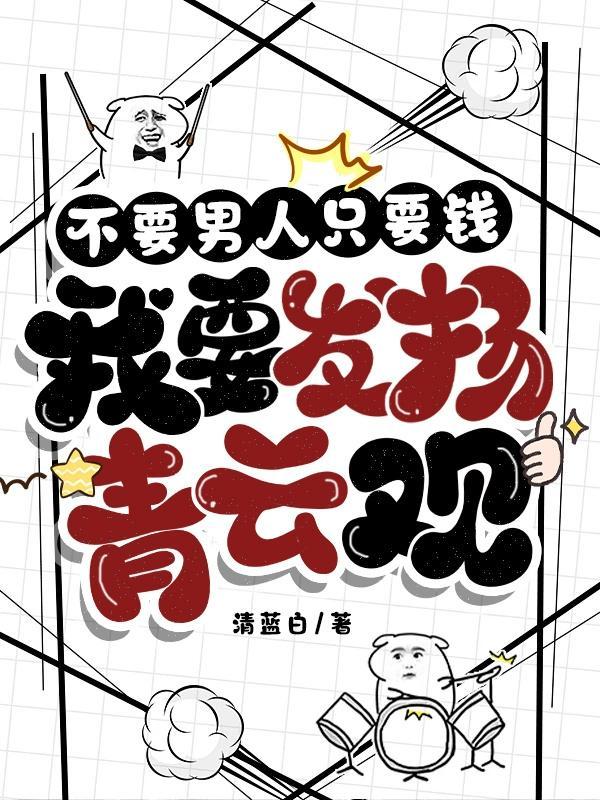深度文学网>我回科场捞人上岸[科举] > 第36章(第1页)
第36章(第1页)
虽然顾家殷实,但小公子本人可是两袖清风。
他甚至想过,实在不行就从家里那七宝帐子上扣些玉石玛瑙典当。
但看着黄五,顾悄突然福至心灵,有了一个更大胆、也更崭新的思路!
他为什么要等自己考了秀才再开书院?
想他当年开班,小小一个地方状元、两个普通公务员岗位上岸资历,都能在一众讲师里傲视群雄、叫得山响,如今出了两个全国状元的小学,这活招牌怎么可以白白浪费不变现!
顾氏族学束脩收得不多,唯一的门槛是需要一个辈分高的引荐人。
他完全可以打着他爹的旗号,先揽下这桩稳赚不赔的中介生意。
摸着银票,顾劳斯笑眯了眼。
甚至黄五那有碍观瞻的脸,此刻也仿佛bulgbulg闪起金钱的万丈光芒。
顾悄愿称之为——招财金蟾自带光环。
顾悄隐隐有些兴奋,从桌上一沓大历宝钞中摸下来数额不小的两张,轻咳一声,“用不了那么多,我回去替你问问,如果不成,原数退回。”
不是准话,黄五略有些失望,闻言也只得收起剩下宝钞,道了声劳烦。
顾悄揣着热乎的钞子,准备说几句场面话就各自散了,却听到那“富贵闲人”终于开腔,“这番我下江南到徽州,是受故人所托,寻一件器物来头。听闻小公子最擅杂学,见多识广,不知小公子可愿帮我一把?”
他声音清润,先前的倦怠之意,尽数化作了撩人的慵懒,听得顾悄耳根有些酥麻。
除了音色不同,他说话特有的腔调、细微停顿乃至呼吸气韵,竟与谢景行十分相似。
他不会听错。
历史学院的每一场演讲、朗诵、晚会,但凡有谢景行开腔的地方,顾悄都跟小迷妹一样场场点卯,他甚至熟悉谢景行的声音,远远胜过他那张芝兰玉树的脸。
毕竟,近视学霸再勇,也干不出学校活动的舞台下,带望远镜替学长加油的蠢事。
而有机会近距离看那张脸的时候,顾悄只会紧张到双眼失焦,眼神乱飘。
惊疑不定之间,他不由抬头又看了谢昭一眼,正与那人深邃目光撞个正着。
那双眼里,带着上位者漫不经心的审视,或许平静之下还藏着诸多情绪,但顾悄肯定,没有独属于谢景行的温情脉脉。
脑子里胡乱转了一通,顾悄甚至没有听清他问了什么。
谢昭眉峰一蹙,登时沉脸,“昨日顾家三公子还张口闭口礼不可废,今日就这般健忘,连与人应答最起码的尊重都不记得了?”
顾悄被问得有些羞窘。
好在原疏体贴,凑到他耳边准备低声提醒。
谢昭见状,气压更低,语气更凉,“昨日种种,并今日所见,想来顾三公子是不大看得起在下。”
顾悄心中响铃大作,职业雷达滴滴警报:不好!发飙了!
他几乎条件反射地挂起一抹如沐春风的笑,亲自用包得如粽子般的手,捧了一杯香茶送到谢昭跟前,陪着小心道,“那肯定不能,只是刚刚听着谢大人声音,只觉得梦里依稀,似乎哪里听过。因此有片刻失神,是悄的错!是悄的错!”
顾悄带公考的时候,没少遇到事儿事儿的学员,一点小事吵吵起来能喋喋不休一个下午,久而久之,他练就了一身面对面神游的本事,这样当然免不了经常被抓包。
但每每他微微笑着,一脸温柔地向着对面轻声细语解释,“甚是熟悉”“是不是哪里见过你”,诸如此类的骚话一出,对面无不偃旗息鼓,红着脸道完歉就飞奔出他办公室。
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他最常用的搪塞梗。
没想到拿来对付谢昭也挺好用。
眼见着阎王脸上拨云见月,甚至抬手接过了茶正要送往嘴边,顾悄赶忙又伏低做小接了句,“毕竟我还小,若有哪里冲撞大人,您也不要跟小孩子计较嘛!”
谢昭喝茶的动作,蓦然顿住了,握杯的手背,甚至隆起几根青筋。
刚刚见晴,又急转阴雨,这般阴晴不定,令顾悄的笑也僵在了嘴角。
他满眼无辜,压根不知道自己又说错了什么。
好半晌,阎王才抿了口茶,淡淡吐出一句,“呵,小孩子……”
那气音低沉又暧昧,犹带三分嘲弄,个中意味,怕也只有谢大人自己知晓了。
顾悄擦了擦汗,虽然不懂谢昭深意,但耳根却不自觉红了一片。
古人早慧,命也短,十六岁娶亲的比比皆是,这年纪自称小孩子,多少有些厚颜无耻了。
二人间气氛诡异,黄五不由头大。
念及自个儿那点不足为外人道的私心,他不得不开口替顾悄救场,“谢大人下徽州,是受人所托,找一件犀皮漆器的手艺人。”
说着,他从袖袋里取出一枚绛红色松鳞纹脂粉盒放到桌上,“这件旧物,谢大人寻了很久,才依据瓷底刻记,辗转打听到出自徽州一位老工匠。只是我们寻过去的时候,老工匠早已去世,他的子女也不知流寓何处,只打探到大约迁居到了休宁一带。顾家在休宁根基深厚,各处乡里也有经营,因而想请小公子帮忙打听一二。”
那盒子只女子手心大小,乍一看与普通木匣子无甚区别。
怪异的松纹,顾悄觉得有些眼熟,一时却想不起来哪里见过。
能叫谢昭辛苦四处探寻的,肯定不会是什么简单物件。
他并没有多说,只留了个心眼,点点头道,“我会留意。”
黄五又喋喋不休交代了一番,这才领着那尊煞神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