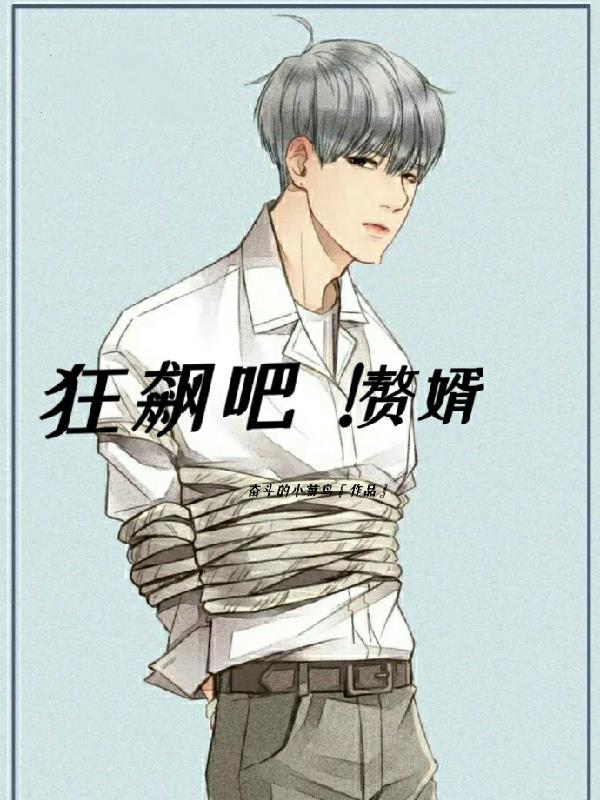深度文学网>被典开局君临天下储君 > 第140节(第2页)
第140节(第2页)
大齐只贱籍无法科举出仕,商贾司空见惯,世家?大族也做经营买卖,天?子内藏库的钱财,也来自于商。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的地位,还?是高于商贾。读书?人能写出锦绣文章,见识不凡,但在庶务上,比如柴米油盐等,就?远不能与商贾相比了。
大齐还?是以农为本,文素素与几人细谈,了解他们的买卖经营,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之法等。
从早谈到晚,文素素宴请赏赐几人,将其送出宫。
酷暑已经过去,月色下,夜里的风吹到身上舒适宜人。沈相林尚书?几人缓缓走过护城河的桥,无人说话。
秦王太妃与文素素多说了几句话,走出来时,见到他们几人还?在前面,她加快了脚步,沈相林尚书?走在最后,听?到声音回?头,停下脚步见礼。
“怎地,听?了民间的实情,被震撼住了?”秦王太妃曲膝回?礼,故意笑盈盈问道。
沈相讪笑了下,道:“着实如此,几人胆大敢说真?话,言之有物。平时我们能看到,听?到的,皆是经过了挑选,送到面前,有失真?实。”
秦王太妃道:“不止是沈相,我以前也没?遇到过。如你?我等人,随着身份地位日渐升高,办事就?越顺当,各种关节,不打自开。”
林尚书?干笑道:“秦王太妃说得是,今日我是开了眼。唉,以前总觉着自己对民生民情了若指掌,实则离得十万八千里,真?真?惭愧呐!”
沈相道:“还?是太后娘娘想得深远,你?我皆不如也。”
秦王太妃道:“酸儒总拿太后娘娘的出身做文章,太后娘娘大度不计较,平时太忙无暇顾及。要是我遇到了,定要打碎他的狗牙!一群混账东西,他们何来的脸骂,他们既嫌弃太后娘娘的出身低,他们却连这般低出身的都不如,纯属一群无用的蠢货废物!”
酸儒读书?人对文素素的抵触,小报上的各种八卦离奇消息,沈相也看到了一些。
他也被小报编排过,并不当一回?事。不过,秦王太妃从不无的放矢,她这番话,定有深意。
沈相沉吟了下,道:“太后娘娘常说,要是不懂之处,就?直接发问,莫要自己胡乱揣摩,猜错做错事就?麻烦了。秦王太妃的意思,我一时想不明白?,还?请秦王太妃明示。”
秦王太妃哼了声,道:“我就?是替太后娘娘不值。太后娘娘以前只是弱女?子,自己做不了主,被兄长卖掉,再被夫君赁出去生孩子。沈相,酸儒也好,读书?人也罢,都是读圣贤书?之人。圣贤书?上可有这样的道理,圣人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没?读进去也就?算了,连血脉亲情,人伦纲常都不顾,将妻子典出去生孩子,简直就?是畜生不如!”
沈相与林尚书?神色一震,彼此互看一眼,沈相斟酌又斟酌,道:“唉,秦王太妃也清楚,这件事吧,就?是穷困,无知闹出来的后果。活不下去,为了糊□□命,将妻子典出去换钱。娶不到妻子的,一户人家?几兄弟,共同娶一个妻子,凑钱典妇人生孩子,绵延子嗣。大齐穷困偏僻之地,如此般的事情遍地发生,民不举官不究,一旦发生争执,官府以契书?为证。“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就?是朝廷要管,也难以杜绝啊!”
秦王太妃冷笑道:“太后娘娘生与江南道,江南道可不穷。咱们都心知肚明。穷生子,子再生子,为了那点香火,坏事做绝,闵州一地盛行的‘契兄’,才是真?正的断子绝孙,偏生不只仅仅因着子嗣生计,就?是为了脐下三寸丁的享乐!”
闵州府一地为了得男,溺亡女?婴之风尤甚。男人娶不到妻,便?将家?中儿郎扮做“新娘”模样出嫁换取彩礼,两人谎称“契兄”过日子。
沈相林尚书?干笑,两人都不敢接话。
秦王太妃干脆地道:“反正我不管,太后娘娘的遭遇,你?们只当做八卦看,我却万万不肯!”
沈相琢磨着秦王太妃话里的意思,苦笑道:“秦王太妃仗义,我等也不能落后。”
秦王太妃道:“有沈相这句话就?够了。时辰不早,我先走一步了。”
沈相与林尚书?望着秦王太妃离开的背影,林尚书?回?过神,小声道:“沈相,税司之事,官员,可是已经定了?”
“近日应当会定下,林尚书?急甚?”沈相道。
税司已是板上钉钉之事,江南道漕司程弼已被召唤进京,算着路程,这两日就?应该到了。
至于前去江南道的税司官员,文素素虽未最终决定,沈相心中有了大致的猜测。
有好些消息灵通的人来找林尚书?打探,想要捞个肥差。如今不比从前,林尚书?皆找借口推脱了。
文素素可不是能糊弄之主,手腕凌厉,要是敢误了她的事,她绝对不会手软。
璟郡王邱大学士孙子被请到府衙问话,在牢里客客气气被关了数时日,放出来洗澡更衣,让他们放松了两日,重新又被请了进去,如今还?在问着话。
邱大学士与齐瑞一样,称身子不好告病在府。方参知政事也学乖了,朝会上没?再出头。
两日后,程弼风尘仆仆进了京,先进宫回?差,青书?将他直接领到了承明殿。
文素素打量着程弼,身形中等,不苟言笑的脸,看上去沉默稳重。
“程漕司辛苦了,请坐。”文素素道。
程弼拱手谢恩,四下略微张望,大殿内只有文素素。他神色微楞,在下首椅子上坐下,青书?奉上茶水,他礼数周全,欠身道谢。
文素素道:“程漕司此次进京,程漕司是独自回?来,还?是家?人一道随行?”
程弼道:“回?太后娘娘,朝廷旨意下得急,臣恐耽误了差使?,独自赶回?了京城。”
文素素道:“朝廷旨意也不算急,程漕司在江南道任上已六年有余,这些年吏部考评皆为上等,早该动一动了。”
程弼面色不变,欠身应是,“臣该年后进京述职,接到旨意,臣着实未曾料到,没?来得及收拾。”
漕运的船南来北往,消息最为灵通,朝廷为何召程弼进京,他如何能不知。
程弼真?是沉得住气,绝不多言多问,等着文素素先开口。
文素素唔了声,道:“程漕司在江南道这几年,且说说江南道如今的赋税漕运状况。先报喜吧,说说好的一方面。”
程弼眸中意外闪过,沉吟了下,道:“江南道自古富裕,产蚕桑,茶,盐,粮食。水路陆路四通八达,靠海的码头,常有海船来往,番邦商人前来大齐,带来新奇的番货。农与商皆繁荣,江南道的赋税向来居大齐之首。”
文素素不置可否,道:“那再报忧,说说坏的一面。”
这次程弼没?再那般快回?答,斟酌了下,方缓缓道:“臣不明白?娘娘的意思,娘娘可是对江南道的赋税不甚满意?”
文素素道:“满意,又不满意。”
程弼怔住,文素素道:“大齐仰仗江南道的赋税,只江南道的赋税,对大齐来说远远不够。刑部大理寺关于江南道的命案,越来越多。送到刑部大理寺的命案卷宗,只是一部分?,极恶的案子,能判定意外,或者与命案无关的死?亡,应当还?有不少。”
“臣领着漕司的差使?,事关治安之事,姜宪司方清楚。”程弼答道。